當跨界已成戲曲表演藝術的趨勢,2025臺灣戲曲藝術節特邀米雪、曾慧誠、黃宇琳三位跨領域藝術家暢談如何從各自的專業/舒適圈,進入不同的領域/劇種,進一步反思傳統是什麼?越界是什麼?有界還是無界?
米雪:歌仔戲多樣化的養成奠基跨界的養分
米雪出身新協興歌劇團,2004年以《王昭君》獲得戲台大車拼──高雄縣歌仔戲匯演「旦角──最佳演員獎」。長期在秀琴歌劇團擔任演員、編劇與導演,亦是國寶藝師小咪及王金櫻的文資局藝生。曾獲第26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入圍第34屆、35屆傳藝金曲獎。2023年被《PAR表演藝術雜誌》譽為「一人千面」。 |
|---|
 米雪
米雪
2024年12月,米雪自編自導的穿越古今歌仔新調《化身》演出,這是她成大戲劇碩士學位學程的畢業製作。「每一改轉世攏是不同的角色」,《化身》雜揉輪迴投胎、穿越時空等元素,當主角們在時光中輪轉,米雪也感到自己身為演員,每次演出都如「化境」,在不同故事中說出別人的心聲。她笑言:「我的靈魂真的沒在休息。」而支撐米雪自由跨界的養分來自兒時父親的培養,出身歌仔戲世家的她六歲開始登台。從「開聲」(開嗓)開始第一步,父親手彈三弦,一句句教唱【觀音得道】(又稱【望月詞】),接著學習融入情緒,再學最難的哭腔。
練完「開聲」後,進階到生旦兼學,每種曲調都要練。小生練【大調】,要把聲音打出去;小旦練【背詞仔】(又稱【倍思調】),將聲音稍微闔起來,開嗓跟閉嗓的音調不一樣。俗諺云:「一聲蔭九才,無聲甭免來。」歌仔戲演員的養成從學唱歌開始,接著學腳步手路──擋壁(倒立)、凹腰(下腰)、搟加官(前翻)、搟小官(後手翻)、搶背(翻滾動作)等功夫。生在兼容並蓄、靈活多變的外台戲班,米雪不只要學本行的歌仔戲,南管、北管、京劇要會,流行歌、日文歌也要練。多樣且豐富的學習與訓練是米雪的儲備,往後演任何角色都能活用。加入秀琴歌劇團後,米雪開始接觸編劇,修改戲齣中不合理的情節,也帶給觀眾新鮮感。
米雪亦積極參與跨界表演,自不同領域的表演藝術中得到刺激。從現代劇場、舞蹈劇場、跨界戲曲,再到2021年的電影《高山上的熱氣球》,米雪在片中飾演男主角阿文的母親。監製王育麟曾問米雪:「歌仔戲等公車會安怎等?」米雪擺出身段:「我會踏跤(踏步),身體會提起來,腹肚收起來。」接著左右顧盼,手一比一攤:「公車哪會猶未來?」對歌仔戲來說,再自然不過的動作,在電影中卻顯得突兀,兩者大不相同的表演形式也是跨界時的挑戰。 2024人權藝術生活節的《鶯鶯》也是米雪印象中深具挑戰性的一次跨界演出,歌仔戲結合南管與現代劇場獨角戲,女主角鶯鶯在白色恐怖壓迫下無法演歌仔戲,無路可走的她只能當妓女。作為獨角戲,與恩客的對手戲只存在於米雪的自說自話中,唯有電燈閃爍代表對方的反應。缺少對手演員使米雪十分茫然,因此她仔細設定他的位置、高度、視線等細節,在現代劇場追求自然寫實的表演風格中,不能演得太用力,她需要學習在演出中全然放掉,深入角色靈魂。
米雪樂於嘗試不同表演方式,注意不同表演藝術的眉角,將身上的功都放下、鬆開,在跨界過程中發揮想像、進行反思,突破壓力與界限,無界、有界,其實不存在那條線。
曾慧誠:異中求同——尋找音樂劇與歌仔戲共通的本質
曾慧誠大學主修聲樂,畢業後赴美攻讀音樂劇表演,取得紐約大學音樂劇表演碩士、美國音樂戲劇學院(AMDA)音樂劇表演文憑。2007年成立「躍演劇團」,執導《釧兒》、《勸世三姊妹》等揉合臺灣文化底韻,且廣受好評的音樂劇。亦與尚和歌仔戲劇團合作,執導《不負如來不負卿》、《田都班的最後一齣戲》、《情定化城寺》、《紅塵觀音—─夜琴郎》等戲曲作品。 |
|---|
 曾慧誠
曾慧誠
從小接受西方音樂訓練的曾慧誠與戲曲的第一次接觸,源於2008年期望發展音樂劇《釧兒》的初衷。《釧兒》創作發想來自澎恰恰,這個情節簡單但情感豐富的人鬼戀,構建在一個不敢搬演《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歌仔戲班上。將西方音樂與歌仔戲曲調結合的構想吸引了曾慧誠,不料嘗試後才發現:原來自己離歌仔戲這麼遠!
《釧兒》初始找了位年輕的劇作家寫上半場,即使文字、情感、結構都對,但故事怎麼看都像發生在臺北東區,讀來就是怪,只得暫時擱置。恰好遇上想要跨界做音樂劇的尚和歌仔戲劇團,曾慧誠便去幫他們上了五堂音樂劇表演課程。隔年尚和歌仔戲劇團梁越玲團長詢問他願不願意挑戰執導《不負如來不負卿》,懷著想了解歌仔戲的心情,小白兔一頭栽入叢林。《不負如來不負卿》描繪東晉的鳩摩羅什遇上三百年後韓國的元曉,兩位著名譯經人跨越國家與時空的藩籬,在雲端展開愛慾與修道的辯證,劇中複雜的時空交叉迥異於曾慧誠對歌仔戲的既定印象,令他大開眼界。而這齣歌仔音樂劇由李哲藝作曲,不受傳統歌仔戲曲式拘束,每次前奏好像歌仔戲就要開唱,卻又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歌仔戲演員與音樂劇演員的攜手合作更使該劇展現有趣的跨界質感,如何統合歌仔戲與戲曲演員呼吸不同的節奏及質地,更是身為導演的挑戰。戲曲演員身上的功是他們很好的工具,外在公式影響內在;現代劇場則是內在影響外在,導演的工作在於讓演員理解角色的經歷與狀態,協助演員釐清、建構自己與角色之間情感的掛勾。
曾慧誠與尚和歌仔戲劇團至今已合作九部作品,在合作幾次後,他驚覺歌仔戲與音樂劇原來這麼相似!「天啊,我花了這麼多錢去紐約學音樂劇,怎麼概念在臺灣?」音樂劇偏向概念化、寫實,故需在情節中創造衝突,推高情節與角色情感,最後在高處進歌,展現大情感、大情緒;歌仔戲則是演員在情緒高點「喊介」,立刻下音樂進歌。戲曲演員會將角色心裡所思透過身體展現,透過程式化的表演傳遞,芭蕾舞也是如此,東西方使用身體的概念彼此相通。音樂劇在編排舞蹈時,身體與行動都來自歌詞的驅動,音樂只是輔助;平常大家數拍子12345678,但這招對歌仔戲演員沒用,他們是對「字」。剝去外在的形式,歌仔戲與音樂劇核心概念殊途同歸,都在做戲劇跟文字傳達的身體延伸。
累積歌仔戲經驗後,曾慧誠再次回到念念不忘的《釧兒》,經由梁越玲的編劇,歌仔戲團團長之子阿強與戲迷釧兒無法相守的戀情與《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情節「夾得更緊」,在〈別窯〉與〈回窯〉之間是超越時光與生死的承諾與等待。《釧兒》將西方音樂融合東方戲曲身段,曾慧誠難忘2015年第一次在衛武營戶外試演時的感動──這是百老匯舞台上看不到的演出,立基於自身文化根源的跨界誕生了強大力道。
2025臺灣戲曲藝術節,曾慧誠再次攜手尚和歌仔戲劇團,推出《叁拾號夢.戲神養成記》,以戲團老班主彌留之際拉開序幕,人生走馬燈一幕幕展開,穿梭於時空之中,藉由蒙太奇寫法,編織一段段夢境與回憶,闡述對戲曲的愛。該劇新穎的劇情結構令曾慧誠想到1970年代誕生於百老匯的「概念音樂劇」(Concept Musicals)──運用不同故事去闡述核心主題。
於曾慧誠而言,跨界最重要的是尋找共同的連結,西方音樂劇與傳統戲曲這兩個看似相同又具備不同文化底蘊的表演藝術,底層掛勾的結構與共通邏輯在哪?尋找「同」而非「異」,使跨界創作的過程更富趣味,也促使演出產生更不一般的質感。
黃宇琳:打破後,帶著跨界的養分回歸原有的專業
黃宇琳工青衣花旦,復興劇校國劇科第24屆宇班,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畢業,有「臺灣京劇小天后」之稱。表演觸角延伸至影視、現代戲劇、崑曲、歌仔戲、相聲曲藝等領域。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第51屆文藝獎章國劇表演獎、第25屆傳藝金曲獎「最佳個人表演新秀獎」。入圍第51屆金鐘獎「新進演員獎」,第31屆、35屆傳藝金曲獎「最佳演員獎」。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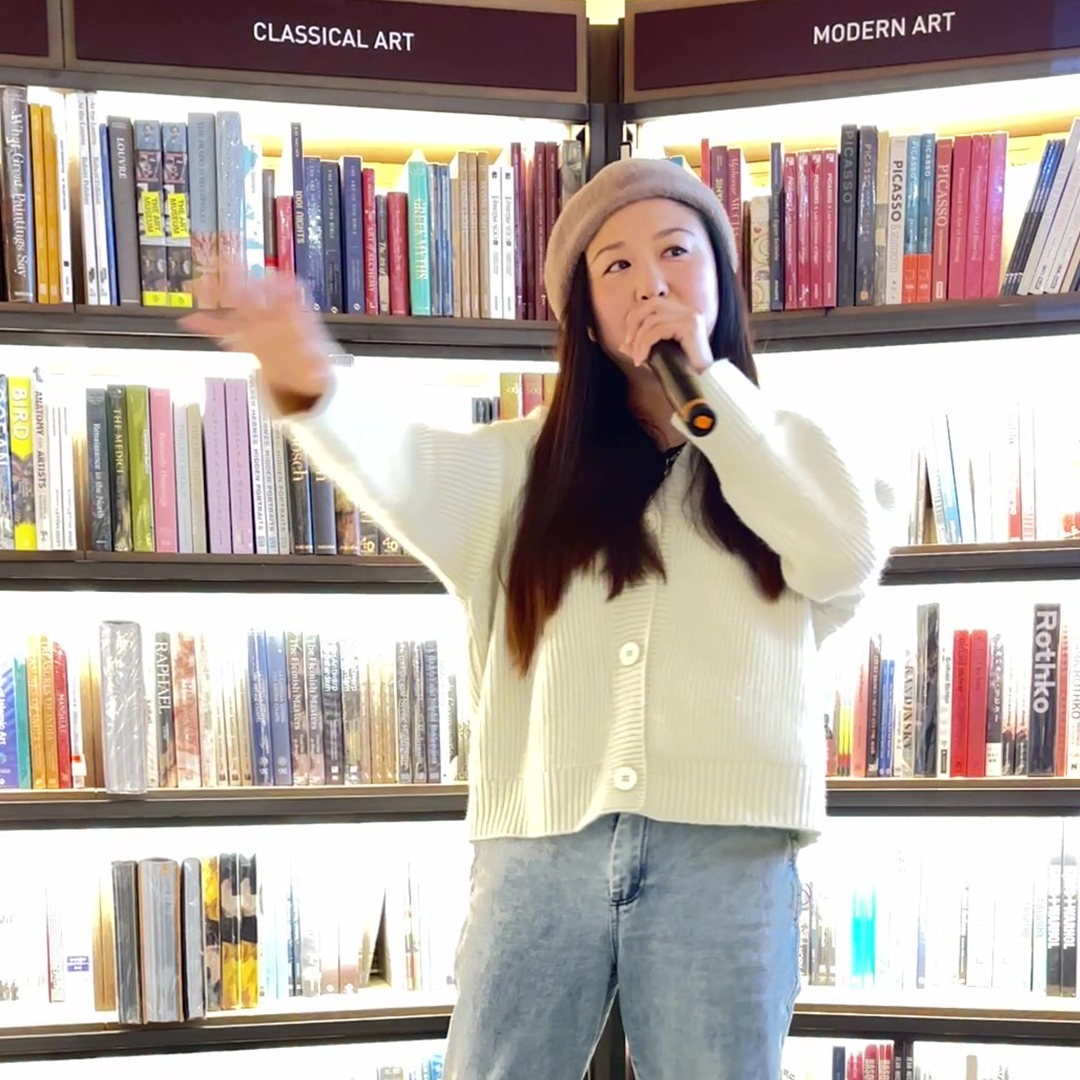 黃宇琳
黃宇琳
1997年夏天,大學一年級的黃宇琳參與了屏風表演班《京戲啟示錄》,遇見恩師李國修。那是個痛苦的夏天,黃宇琳過往立基於京劇的表演方式被通通粉碎。
《京戲啟示錄》以「戲中戲中戲」的套戲結構呈現,「風屏劇團」團長「李修國」堅持推出新作《梁家班》,而京劇團「梁家班」一邊排演《打漁殺家》,一邊面臨藝術上的衝突與生存。黃宇琳在劇中扮演她自己「黃琳宇」、梁家班的小女兒「丫頭」及《打漁殺家》的蕭桂英。當劇中「黃琳宇」要對有婦之夫「李修國」告白,現實中的黃宇琳過不去心中的坎,對尊敬的老師演出告白,李國修也理解她的狀態,故意在排練時不走這段告白戲。蕭桂英是黃宇琳的舒適圈,丫頭演來尚屬得心應手,但她也常忘記梁家班的時代背景是民國,她出場的步伐依然帶著京劇鑼鼓經的節奏。李國修不直指問題,只說「再鬆一點」。黃宇琳困惑於老師為什麼不明說,而是讓她重來十幾次,在眾人面前不停被打斷使她情緒滿溢。預期自己會被罵的黃宇琳只等到李國修讓大家休息一下,大家連忙來安慰黃宇琳。再演還是不行,在眾人圍觀的心理壓力下,黃宇琳忍不住崩潰大哭。黃宇琳看見導演椅旁的垃圾桶,就趴在那哭,眼淚滴進桶內,來得太猛的情緒使她邊哭邊抽搐。
「你現在一邊哭,耳朵聽我講。」李國修開始念「黃琳宇」的台詞:「修國,我一點都不想離開你,你知道我們全家要移民了嗎?」「老師,我還在哭耶。」「對啊,你哭你的,你耳朵聽我講。」老師的理性是這麼殘忍,但黃宇琳也在那瞬間明瞭:原來她以為的「放鬆」仍是「武裝」。對戲曲演員來講,表演是裝扮,也是感到不安時的武器,她以為自己掩飾得很好,其實什麼也沒放。
哭到眼睛腫的黃宇琳帶著功課回家,李國修要她想像明天她的生命會結束,看她怎麼過這最後一天。黃宇琳宛如腦袋被開了個洞,掀開蓋子有熱氣冒出,當她騎摩托車準備回家,她頓悟世界是如此可愛,萬事萬物都使她悲從中來,不由在路邊嚎啕大哭。激動的黃宇琳打給同學,分享今晚排練的種種,對方覺得這一切瘋了,「我要是你,才不鳥這件事。」黃宇琳卻感到有什麼一直往腦袋衝,也使她心裡滿滿的,那是真實卻難以承接的,當明天再次走進排練場,即使無法用言語表述,她仍會有個屬於她自己的答案。
隔天李國修溫柔地問她狀況,黃宇琳答:「你直接說,我是不是瘋子?」「你只是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是個感性的人。你知道你的寶藏是什麼嗎?你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況,這是你的禮物。」黃宇琳忍不住抱著老師大哭:「你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抽那麼多菸……」
2013年《京劇啟示錄》在上海重演,李國修宣布他得了大腸癌,黃宇琳秒回當年,再度抱著他哭:「你有想過為什麼我那時候會要你保重身體嗎?」李國修幽默笑道:「對啊,但我還是焦慮地一根接一根,沒有辦法。」往事重疊再起,師生也憶起當年排戲,他叫她唱《打魚殺家》裡蕭桂英的唱段,她一開口他就哭了。「老師,你為什麼要哭?是我哪裡表現不好嗎?」原來他在做角色功課,揣摩「李修國」面臨「黃琳宇」炙熱的情感,卻不能接受,他相信她有更好的前途。
黃宇琳大受震動,老師示範了如何用生活中唾手可得、無須與人言說的方式做演員功課,黃宇琳也學會從生活中擷取素材,作為角色關係能快速堆疊的材料。那年夏天,黃宇琳被粉碎後又再重組。她以為她參與《京戲啟示錄》可以成為舞台劇演員,作為演出陣容中唯一的現代劇場新鮮人,黃宇琳覺得自己像老鼠屎。但李國修不管她怎麼認定自己,第一次演舞台劇不構成「不會演」的藉口,面對新事物本該學習吸收,不能把做錯視為理所當然,他期許她帶著新的養分回去,成為一個「不一樣的京劇演員」,而演完這齣戲更稱不上結束,每次回想都是收穫,那不是最終解答,身為演員注定擁抱這橫跨一生、無窮無盡的追尋。
在屏風的這段經歷,黃宇琳學到何謂「演員」,不同於戲曲演員往往身體力行,功夫背後蘊含身體負荷,李國修帶給了她一套完整的觀念──身為演員的基本素養、當演員的追求、面對自身與角色的心態調適。重組再出發的黃宇琳帶著恩師的教誨,持續探索各種表演藝術領域,走在這條沒有終點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