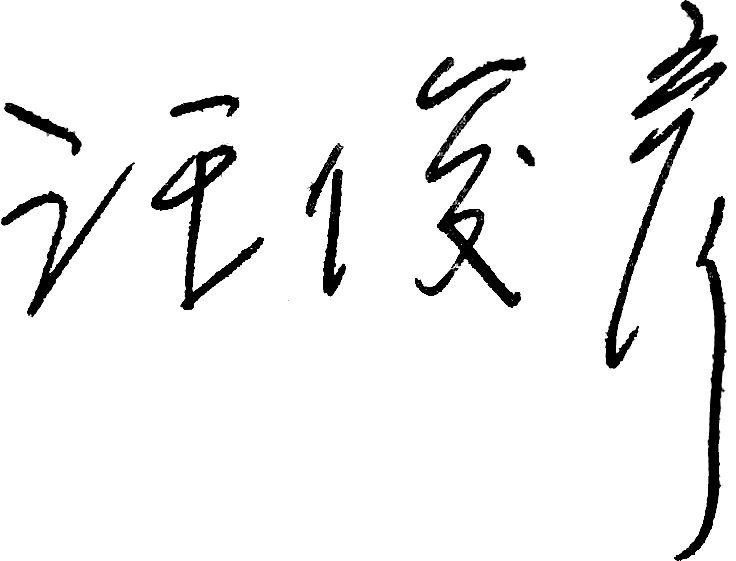廿世紀初期的戲曲是個革命的年代,無論在中國或臺灣,戲曲回應了劇烈美學範式的變化,從歷史與觀眾身上認知了自身的前衛性格。世紀中,世界進入冷戰格局,冷戰是一個讓革命不能想像、也不能發生的時代,而今日的我們,無論是戲曲或是戲劇,無論是現代或是傳統,仍然大程度地受制於冷戰的美學認識論。革命需要不滿,不滿則是持續創造劇場與觀眾關係、創造美學能量的動機與基礎。2025年「乙巳革命」的實踐,以戲曲夢工場試圖指出戲曲就是革命的繼承者與發動者。
革命的當代系譜:世界即革命
馬克思在1851年完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隔年發表在《革命》(Die Revolution) 月刊。今天我們所認識的「革命」概念,與這個現代性的「世界革命」生成密不可分。儘管在中國古代典籍裡即有革命的用法,尤其在天命與民心等政權轉換的法定性或是自然秩序的交替等,但透過世界革命論的出現,無論是英國光榮革命(1688)或是法國大革命(1789),「革命」進一步在翻譯的關係之中重新相互構結,形成大多數人認知中的革命:叛亂、顛覆與淘汰,但也仍不脫漸進、改革與延續的時間性相互參照。換句話說,「革命」雖然暗示了激烈的衝突,但其意旨仍存在尚未全然一致化的多元系譜;當「不斷革命」成為理解現代世界的根本生產性的基礎時,戲曲同時期所面臨各種觀眾、美學、製作與演出的挑戰,被期許探索未來可能性的實驗,其核心即是面對歷史物質的現場,進行不斷革命。
自進入現代世界以來,伴隨著觀眾對於劇場認知的轉變,戲曲一方面以架接現代戲劇作為回應,另一方面又弔詭地以堅守傳統作為延續戲曲生命的號召。兩種走向截然不同方向的策略,竟出自於對同一個世界物質現實的回應。往後,所有的問題集中擺盪在被限定的現代與被限定的傳統之間,隱蔽了作為始作俑者的現代性其種種缺陷,也隱蔽了正視歷史現實的能力。以革命為題,說明了當代戲曲並未遠離自現代世界現身後的世界格局,甚至以各種跨界與跨域為名之下,幻想某種已突破的狀態,反而讓戲曲局勢更為嚴峻。而廿世紀長達半世紀的冷戰臺灣,又加遽了正視戲曲世界革命的困境。以「民主自由/社會共產」強制對立的意識形態主宰一切行動與實踐標準,進一步固化正統性的話語,而迴避了戲曲回應世界革命的內在精神狀態;或者我們也可以說,不只是戲曲的創作者或實踐者如此,也是同時期觀眾的意志主導了冷戰戲曲的美學,也延宕了反思帝國與殖民現代性下與其外,戲曲的種種限制與未激發的能量。當戲曲不斷被塑造成特殊與地方的民族或古典狀態,包裹在維護傳統的語彙之中,反而失去戲曲作為劇場表演,從來在溝通任何觀眾、溝通世界的基礎上成形。「乙巳革命」的提出,來自於召喚戲曲作為世界的,而非特殊的歷史實踐與認識。
然而,即便在這場世界革命的大潮流下,戲曲的劇場展演在現代戲劇標準範式的「威脅」與「比較」之下,開始全面性地進行了幾乎可以以「革命」視之的自體改造行動,延續至今;與此同時,也創造了更豐富的劇場經驗、行當表演、流派與經典。換句話說,當代戲曲身上所繼承的DNA,以及觀眾所感知的表演,都可能仍帶著百年前那場革命的熱情;同時期的臺灣,客家戲、歌仔戲回應整個世界與社會結構變動,也一躍成為深受普羅觀眾喜好的表演,就此層面而言,亦不可不視為一場情感革命。
劇場需要革命,革命需要什麼?
革命需要不滿,不滿是對於觀眾與創作者對於劇場性的再確認。本次「乙巳革命」,以天干地支記年的標題與革命訊息連結,期待就某種未知的暗示性,提示戲曲夢工場的創作者與觀眾同為每一場、每一刻歷史革命的啟動者。革命是理念也是行動,隱蔽革命的慾望,不是用來作為美學上缺乏突破的話術,實則壓抑了戲曲所有參與者共同感知現實的能力。戲曲夢工場「乙巳革命」就戲曲目前的政治、情感、技術、手法、議題等的限制與開展,讓其自身的革命因子所投射出的能量,連結世界與外在環境,作為行動。
百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浪潮,從國家政治到日常生活,不僅僅對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戲曲與觀眾產生影響,拉開地緣視野的限制,東北亞的日本、東南亞的南洋都共同捲動在這一場戲曲革命的風暴中,在知識、典律、媒介、座標等再衡量中,重新價定與創造了戲曲的新內涵。當我們僅僅聚焦在關注現代戲曲之於東/西方的問題之外,世界其實還有他方的革命。在這次演出製作中,我們嘗試在所謂「現代與傳統」的論爭外另闢第三路徑,也透過反覆與重複進入歷史的歧途,一方面回應2023年時,我承接戲曲夢工場策展的第一年主題「前衛當行:以戲曲提問歷史」,另一方面也明白拒絕不斷以自恃的「現代與傳統」,或是這兩條路的共謀來識別戲曲的討論。由合作社主持演出的《前方有三岔路口》,脫胎自京劇名段《三岔口》,描述各路江湖人馬如何在極度沈靜的黑暗之中,彼此試探與打鬥,革命在一片黑暗之中起身,但黑暗中,從來不只是兩股勢力,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行好手匯集三叉,在戲曲舞台上摸索第三條路。臺北木偶劇團的《鬧・NOW》,得自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玩耍於天地章法的他,也是布袋戲舞台與演師的心有戚戚。臺北木偶一團除了自身要分化成兩棚,而且還是鬧兩棚、闖三關〈鬧龍宮〉、〈鬧地府〉、〈鬧天宮〉,一場二棚,雙絞競演,三鬧入戲。三人成眾,三是介入,更是重整群眾。戲曲作為革命聚眾的實踐與再現,一直都是仰賴集體行動的。
想像革命那一刻的身旁人與事
革命需要伙伴,來自各種性別、種族與階級的伙伴。「烏犬劇場」長期敏銳地透過藝術,處理真實世界被結構、擠壓的記憶與空間與各種樣態的「人」。戲曲的多樣態,無論在文本或劇種,都以表演摺疊、稜射、再現不同階級、不同歷史的「人」。歌仔戲擅於以情感溝通生命的畫本,將引領我們理解革命行動者的處境,不是僅在摧毀,也不能只以看見自己眼中想成為的樣子為終點。《嘉慶君遊臺灣》曾一再在臺灣歌仔戲史中反覆現身,明日和合製作所《嘉慶君夢遊臺灣》遊走於史料、檔案與現場表演,思考一直扮演著歌仔戲美學形式轉變核心的觀眾,如何隨著在電視歌仔戲與各種歌仔戲表演媒介擔任參與革命的角色,歷史的嘉慶君到底有沒有來過臺灣變得無足輕重,他的各種化身展示了「(假)臺灣人」才是玩弄真假與符號的行家與革命者。
革命需要技術。古巴革命的知名人物「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在義興閣的《英雄製造》中,以他革命前漫遊南美洲的旅行紀錄《摩托車日記》,對照拆解革命後,透過他的形象不斷製造的商品符號,穿梭在今日「不斷革命」與「革命(商品)不死」的技術之間,正視符號替換革命的當下,宛如以不死的戲曲概念替換戲曲實踐的同路。《皇上還沒來的時候》的主角們將在臺灣這個舞台上共演《貴妃醉酒》,演繹著等待皇帝到來的故事,是時候別再問「京劇是不是姓京」的問題了,演出者的京劇身段與肢體動作即時轉化為不可預測的聲響與影像,語言、肢體和生成的符號相互交織,不停流變,皇帝來之前,各種革命的可能都還沒消失,問問今日我們容不容得下思考或許皇帝也是革命軍?
革命的軌跡
三年(2023-25)的策展將在乙巳年總結。從歷史到群眾,再到世界,從對自身的再判讀(前衛當行),到開啟自身聚合化為各種集體之眾的想像(聚眾),最後以正視自身與環境的限制,重啟面對現狀的革命動力。乙巳革命是面對不平坦世界的必須。
策展人